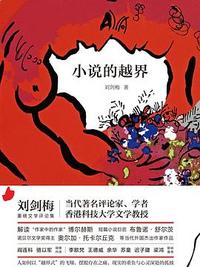阎连科
理论与小说写作的隔膜,一如北方的老榆和一棵南方棚大的榕树,几无可谈的相似之处,使得我们经常在左耳听到作家信誓旦旦地说,我从来不读文学理论书;又几乎是同时,在右耳听到理论家面带讥笑道,当代文学实在难有可读之小说。这种两相对立、互不心往的状况,不仅宛若北方的榆树和南方之榕树,怕也是同一片土地上的野草和菊花、荆棵与野槐,你开你花,我生我叶,并无实质之交错,只是在外人眼里,榆树和榕树都是世间树木吧;野草、菊花、荆棵和野槐,都是人世的绿中之植吧。这样久常的疏离和隔膜,每每使人读一篇或一本能够如渴之饮的文本批评或理论,便会觉得比读了十本、二十本每天都在出版、每日都在书店的货架上摆上或撤下的小说要胜好着许多或太多。
作家等待和寻找如渴之饮的文学批评,如同批评家朝日求找一部可读可言、言而不烦的小说。此间两相的抱怨和根恨,在双方的胸腔之深处,已经怼埋了太久、太深远,只是中国的文化和人情,让彼此笑而不谈并彼此心知肚明地饰而不言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冷笑、隔膜和彼此难有正眼相视的奇情与异状,读到刘剑梅教授这一系列对现代经典的析阅论说时,先是感到有一种隔膜消除的亲近感,后是那种两相根恨如柏林墙样被推翻的豁然和开朗。及至她将这一系列的文章汇编为《小说的越界》后,再一次地集中阅读,便突然有了那种“等到了”“找到了”的喜悦和兴奋。
实实在在地说,很久没有读到过对自己和诸多读者都共同心仪的作家和作品有个人见地或观点相似的理论著作了。《小说的越界》,是一个批评家的私人阅读史,也是这个批评家与作家和读者的共同阅读史。而这其中谈到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几乎都读、却又少有成文的理论去梳理和言说的。《小说的越界》就在这时如期而至了。它既不东拉西扯地去卖弄和装点,也不仰视、膜拜地将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当作耶稣和《圣经》,摆在文学的圣桌上供奉和恭敬。每一篇的阅读和剖析,只是要告诉你“我喜欢和我为什么会喜欢”。亲近、随和,并发自内心去分享,而非因为“我要理论”才去说,才去读,才去引经据典地写出来。原来在文学理论中,“我喜欢”和“我要写”,是这么不同的两件事。前者因为喜欢才去读和写;后者因为要写才去读。当二者都成为理论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前者的文字中,呈出一种自然亲切的欣悦感,后者呈出一种肃严、正经的呆板感。前者的轻松、欣喜一如坐在茶馆、咖啡馆里相遇和聊天,无非彼此见面聊的不是吃饭、穿衣和住房,而是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书;而后者,则如教室中的老师和学生、讲台与课桌样的距离及隔阂。因为后者一上来,老师就对学生说,现在上课了,请大家都拿出笔和本。
再次读完《小说的越界》而收合尾章时,我沉落在这本给我带来喜悦的理论书册里,于是想到这喜悦的渊源出处了—12篇文章,谈到了百来个作家和上百部的书,并不是每个作家和每本书都使我喜爱并欣悦,那么为什么一本理论著作中的文章和通篇之析作,又篇篇会让人感到不间断的喜悦和亲近?如同阅读一部你并不完全喜欢、却又让你一字不落地去品味的作品一样。如波拉尼奥的《2666》这部巨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读完了它?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爱它?到底那些喜爱它的作家和读者,有几个能说出因之喜爱的一二三?大凡一站到人前就谈论波拉尼奥和《2666》的人,我常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脸,试图从那脸上读到一层人云亦云的盲从和虚伪。然而在读刘剑梅的《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篇对《2666》抽丝剥茧的作品分析时,她和她的文章让我那种怀疑的目光变得温和了、释然了,随性并也包容了。直到今天,我都以为《2666》因为作家写作前是为了五部小说而起笔,并非为了一部巨制的面世与出版,所以,当将五部组合为一部时,结构上是有着明显隔离和生涩的,然由于我们对波拉尼奥的写作与离世,深怀着敬重而不去挑剔这一些。所以在几乎所有人都盲目盛赞《2666》时,我总是盯着那盛赞者的眼—也就这时候,恰到好处地读到了刘剑梅的《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来去有据的文本分析了,也是这时我对刘剑梅教授开始怀有了顿为愕然的敬重感。这种敬重不仅是她率先打破了《2666》的伟大连续多年都凝结停留在中文读者和作家嘴边的喧闹上,以一个女性的独有之目光,写出了《2666》对世界、暴力和女人与人的强力、强大的关注和投入,而更在于《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篇论文,使人感受到了批评家的文学情怀是何等重要和关键。一如一个作家没有情怀空写出的小说一样,倘若一个批评家,没有情怀而去析说理论时,哪怕你的才华、聪智大如山脉与海洋,写出来的文章、著作怕也是没有血脉的积木建筑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我们说没有情怀的小说就是没有灵魂的篇章文字,也可以说,没有情怀的理论,同样是没有灵魂的篇章文字。从面对波拉尼奥到面对舒尔茨,从面对舒尔茨到面对托卡尔丘克,再到她面对奥维德和他的《变形记》,这一路的解读和析说,在刘剑梅的文本分析与纵论横比中,我们始终在她的理论述说里,可以真切、清晰地读到她对人与人世的爱,读到她对文学天然的情感与纠缠,对语言创造发自内心的敬重和对孤独写作者无条件的拥抱和同暖。一如她在《文学如何面对暴力》中说的一样:
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非常有力度。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发出呐喊,让麻木的人们为之震颤?那些知识的承载者,是否已经全军覆没,对黑暗的世界无能为力?
这样一段深具现代意义的盘诘叩问的胸腔文字,刘剑梅说的是《2666》,但也同时是她诘问着整个的世界和文学,是她面对文学的一种现代情怀,也是一位女性面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的现代情愫。而整部《小说的越界》,也正是她“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分析与对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