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口气,养三万六千神
紫茄子
连载中· 55.60万字
我有一口气,能养三万六千神!这个世道,鬼不做鬼,人不当人,那我就夺造化,逆阴阳,变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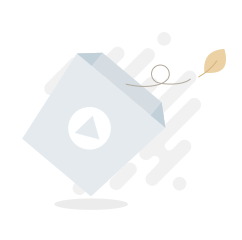

紫茄子
连载中· 55.60万字
我有一口气,能养三万六千神!这个世道,鬼不做鬼,人不当人,那我就夺造化,逆阴阳,变天地!

小七爷
连载中· 6780字
曾经,许愿是个再爱里掏心掏肺的傻姑娘,为了初恋男友,学习他所有的娱乐游戏,迁就他,可最后换来的是背叛,就连一起说好,在同一个大学上学的朋友都背叛了她。 她摘下青涩的校园滤镜,将自己从泥泞的单恋中拔起。从乖乖女到「鱼塘主」的蜕变,是玫瑰长出利刺的觉醒,更是无数个深夜里自我重塑的涅槃。当不同的灵魂闯入她精心经营的「鱼塘」,那些带着试探与征服欲的博弈,却在某场暴雨后,与记忆里十七岁的阳光轰然相撞。 爱不该是囚鸟的金丝笼,而她的花期,终将盛放成永不凋谢的野火。

笑斯人
连载中· 267.75万字
穿越十八年,本以为这是普通古代世界,计划发展成为地方豪强,作威作福。 不曾想,诡异树妖降临,万物采集程序启动,修仙的神秘世界全面打开! 今天开始,我不当地主了!叫我仙人大人,把你们的宝物、灵石、女人通通交出来!

天出
连载中· 60.72万字
【喜马拉雅S级重磅推荐!爆款脑洞悬疑爽文!】 (音效:心跳声急促,电流滋滋声,猛地一声惊雷) 旁白(低沉磁性,充满悬念):千万级直播,影帝出演,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杀人”真人秀,瞬间失控! 当剧本照进现实,当“罪犯”不再是演员,而是来自异界的灵魂——林俊,被强行塞入死局,他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地狱开局?! 【喜马拉雅独家巨献!《极限罪恶追缉:代号幽灵》!年度最燃脑洞悬疑!】 【专业声优团队倾情演绎,带你声临其境,体验肾上腺素飙升的极致快感!】 【立即订阅收听,跟随林俊,杀出一条生路!】

晃晃崽
连载中· 4.19万字
【香江年代文+玄学+娱乐圈+豪门】 被誉为天机门不世之材的柳玄,穿回七零年代,成了渔村里的痴傻少女。父母不仅不是亲生的,还要把她嫁给鳏夫换彩礼,为此她果断报复,逼问出身世后,孤身渡水,朝着河对岸的香江而去。 只是刚到岸边,她就捡到一个男人。男人貌若潘安,八块腹肌,还是个天生贵命,能够挡灾避劫,虽然撞到脑袋人傻了,但也可堪一用。 柳玄带着傻男人,靠着一手卜算的看家本领,逐渐在香江混出了一片天地,帮派大佬头戴绿帽,新任警督恶灵缠身…… 一不留神,她已经成为黑白两道都不敢招惹的存在,就在她声名鹊起之时,傻男人的身世也渐渐浮出水面……

风圣大鹏
连载中· 32.67万字
萧易坤一觉醒来成了修仙界一个野神,从此开启躺平野神生活

日落逾星星
连载中· 141.37万字
云棠出身帝师世家,自小克己复礼,慎独而行。却被继母为一己私欲卖给沈家老爷冲喜。 进门当天沈老爷便一命呜呼,她却在梦中与陌生男人共赴云雨深渊。 噩梦中醒来的云棠忍着羞耻出席葬礼,却发现,梦中那强迫她沉溺情欲的恶劣男人,竟然与自家夫君的长子,战功赫赫的沈筠模样几乎如出一辙! 梦中与他夜夜荒唐的女子,身形竟与父亲新娶的续弦七分重叠,沈筠眼底沉黑隐晦。不仅如此,就连梦中遗落的銙带与玉佩都不翼而飞。 月明星稀,沈筠在又一次旖旎梦中禁锢着云棠的腰肢:“云夫人,夜夜入梦可是不舍本将军?

霜玫瑰
连载中· 24.36万字
双学霸结束三年暧昧争锋顺利升学,返校日当夜月色正好,宜表白,利接吻。 一吻结束,准男友在自己面前变成了章鱼。 只有手掌大小的小飞象章鱼。 萌,但黏糊糊,软哒哒。 一向冷静自持的黎若星,当即惨叫一声把男朋友以完美的抛物线扔进了校园的许愿池。 救命,他有软体动物恐惧症。 - 于洄出身古老的海洋家族,从小就知道若他答应真命天子的求爱,便会获得变异的能力,走上不同于常人的路。 是以那场表白和黎若星,他都只是玩玩而已。 不料报应来了,只想渣一下的娇花变真爱了。 而他的变异进化也失控了…… - “老婆别扔!我把触手收一收还不行吗!啊——” “再贴过来把你触手剁了做铁板烧!” - #我是你豢养的海怪暴徒,忠心不二,永远渴求。#

桂圆儿
连载中· 153.15万字
李锦棠为了侯府操劳半生,死在心血耗损后,可没想到,她所照顾的侯府个个不是人! 耗费心血所救的人是渣夫白月光,散尽家产帮扶的儿子竟不是亲子,亲子被换成最卑贱的奴仆,母子相识不相认。 而她亲生婆母做局逼的她六亲无缘,一边享受她的银子一边骂她商贾之女配不上她儿子。 重活一世,她从孤儿中拣选了亲子,搅的侯府鸡飞狗跳。 努力修复娘家关系,她把昔日逆子捧杀成了自己人,更靠着一双火眼赌石,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一跃而上成为一代传奇翡翠大亨,侯府众人慌了,炮灰怎不听使唤? 为求自保她找上当今权王抱大腿,却不曾想,还未开口,那人竟能偷听到她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