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龙天师
风尘散人
连载中· 779.25万字
“天狗起于垒土,而坠于残霞,天际殷红如血,吉星退于虚无。 苍茫间,一人蹒跚前行,筚路蓝缕,一步一喋血,只余一株荼蘼在身后凋零。” 这是一则无人能解的谶语,可有人说,这是我的命。 还有人说,礼官横涉阴阳,精于墓葬,蒙蔽天机,古之贵人皆葬于其手,以荫后人,终不得好死,我亦难逃。 可是,我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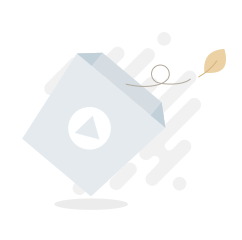

风尘散人
连载中· 779.25万字
“天狗起于垒土,而坠于残霞,天际殷红如血,吉星退于虚无。 苍茫间,一人蹒跚前行,筚路蓝缕,一步一喋血,只余一株荼蘼在身后凋零。” 这是一则无人能解的谶语,可有人说,这是我的命。 还有人说,礼官横涉阴阳,精于墓葬,蒙蔽天机,古之贵人皆葬于其手,以荫后人,终不得好死,我亦难逃。 可是,我不服……

七麒
连载中· 156.58万字
卷王驾到,都给我卷起来,人间在卷,地府也得卷,卷王到来,诸邪退避,我是地府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本书又叫《我在地府混编制》》《地府搅屎棍!》《逆袭,从小鬼到阎王》

深依
连载中· 22.70万字
五年前,江家在一场商业争斗中一败涂地。 江知颜从天之娇女瞬间坠入地狱,公司被夺、负债破产,父母相继惨死… 而她唯一信任的未婚夫也成了帮凶,在后背插刀,毫不留情的给了她致命一击。 那场车祸,她本不想活,却为腹中意外的生命而振作。 她逃离是非,拼尽一切,才得以重新开始。 五年后,生活步入正轨,她带着孩子回来了。 随之归来的,还有仇恨—— 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们,谁也别想好过。 她受过的痛苦,她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哪怕不择手段…

黄粱
连载中· 376.86万字
被开除警队的落魄侦探侯伟、初入警界的新人刑警石晴雪,在命运的安排下,迥然不同的俩人相遇、相识、相知,在消除隔阂中,他们渐渐逼近残酷的真相......

御风楼主人
连载中· 22.06万字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出现的短暂和平时期。但因为多年战乱,死伤惨重,人世间凶灵横行,加之时局不稳,国民政府腐败,老百姓水深火热,魑魅魍魉遍地。玄门术界最大的相术家族麻衣陈家,派出二十岁的陈汉生以相士身份行走江湖,凭借家传相术秘籍《义山公录》和六相全功,解决各种诡异事件。这位被后世尊为“神断先生”的麻衣传人,开启了一场独属于他自己的传奇经历……

乐乐神
连载中· 191.08万字
王初一从小跟着爷爷学习易经八卦,茅山术,剑法,拳法。王初一接触了东北马家弟子马红梅,拜马红梅为奶奶。马红梅临死前,将供奉百仙的堂口传给王初一。王初一仙道双修,杀恶鬼,降恶妖,斗僵尸,度善鬼,与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称兄道弟。

黑色枷锁
连载中· 359.69万字
【50次赌桌上的亲身经历,100种识别千术的内幕方法,教你戒赌防骗!】老千的世界没有运气,只有千术和骗术。有人一夜发达暴富,有人一夜倾家荡产。关键不在于运气,而是在于能否抓住庄家放水的机会。那一次我的失手,将我推入了重重深渊......

青史
连载中· 41.10万字
陈向东刚从乡镇提拔上来没多久,就面临领导被双规的局面。 女友眼看形势不妙,立即转投他人怀抱。 艰难挺过组织调查后,又面临政敌打击报复。 且看如何他一路翱翔,扶摇直上,将瞧不起他的人踩在脚底,陷害他的人绳之于法,最终成就权势巅峰。

仗剑修仙
连载中· 32.68万字
不朽神朝,辖十二古国、诸子百家、各大圣地以及万千修行世家! 北寒萧族,代代族主皆天生神王骨,以一族之力独镇荒古禁地千万载! 神朝下嫁摘月公主与萧族圣子萧凡,大婚当日,摘月公主假死逃婚! 神朝震怒下,萧凡之父萧神王被逼自裁! 萧族内乱在即,自蓝星穿越而来的萧凡,恰与此时觉醒大道因果宝身! 生来无神王骨的萧凡,得大道因果宝身赐予至尊骨! 神朝欺我萧族,那我萧凡便重造一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