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魂特工:强者归来
靖澄
连载中· 9.21万字
王牌特工林渊,为寻失踪妹妹踏入城南诡谲之地,意外觉醒沉睡千年的龙魂血脉。当特工手段与上古龙威交织,阴谋与真相激烈碰撞。黑暗势力觊觎龙血之力,妄图掀起腥风血雨。林渊携觉醒龙魂的妹妹,以雷霆之势横扫强敌,在东方玄幻的世界中,开启一段强者归来、逆天改命的热血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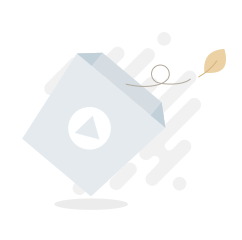

靖澄
连载中· 9.21万字
王牌特工林渊,为寻失踪妹妹踏入城南诡谲之地,意外觉醒沉睡千年的龙魂血脉。当特工手段与上古龙威交织,阴谋与真相激烈碰撞。黑暗势力觊觎龙血之力,妄图掀起腥风血雨。林渊携觉醒龙魂的妹妹,以雷霆之势横扫强敌,在东方玄幻的世界中,开启一段强者归来、逆天改命的热血传奇。

春秋蝉
连载中· 77.68万字
江曼生穿进一本年代文里成为人人喊打的恶女,原主大义灭亲,趋炎附势,恶行累累……江曼生叹了口气,自己堂堂自动化系高级教授,就连噶都是因为考察救学生才噶的好人,摇身一变,成了这个人人喊打的恶毒女配。 这怎么能行!洗!必须洗!就算黑成了煤球也得洗白! 什么小情小爱的,谁愿意爱谁爱,我的爱人是祖国。 六十年代,我国自动化专业刚刚起步,什么都缺,我都领先四十年技术了,此时不报国更待何时? 自动化生产系统!启动! 科技树!点亮! 生产力!拉满! 原本瞧不上她的丈夫周书臣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这位作精妻子竟然成为了一个领域内的顶尖学者。 “老婆,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

nana
连载中· 94.35万字
江烬檀身为一代玄门宗师,渡劫失败后,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成了书中反派的恶毒后妈。 为了避免未来的死局,江烬檀决定花更多时间陪在大反派身边,用母爱感化他! 于是江烬檀带娃上直播娃综,尽显后妈慈爱,把完美人设的影后衬成了反面对照组。 网友们炸了锅,纷纷猜测孩子爸爸是谁。 江烬檀v:请大家不要乱猜测了喔。单亲妈妈。 顾君盛秒评论:? 当天晚上顾君盛直播,小反派突然入镜,慌张地扯着他的衣袖。 “爸爸,妈妈的眼睛尿尿了。” 直播秒被切断,顾君盛表示: “抱歉,要哄老婆去了。” 粉丝们:? 十分钟后,微博崩了。

仗剑修仙
连载中· 36.07万字
不朽神朝,辖十二古国、诸子百家、各大圣地以及万千修行世家! 北寒萧族,代代族主皆天生神王骨,以一族之力独镇荒古禁地千万载! 神朝下嫁摘月公主与萧族圣子萧凡,大婚当日,摘月公主假死逃婚! 神朝震怒下,萧凡之父萧神王被逼自裁! 萧族内乱在即,自蓝星穿越而来的萧凡,恰与此时觉醒大道因果宝身! 生来无神王骨的萧凡,得大道因果宝身赐予至尊骨! 神朝欺我萧族,那我萧凡便重造一神朝!

黑色枷锁
连载中· 366.66万字
【50次赌桌上的亲身经历,100种识别千术的内幕方法,教你戒赌防骗!】老千的世界没有运气,只有千术和骗术。有人一夜发达暴富,有人一夜倾家荡产。关键不在于运气,而是在于能否抓住庄家放水的机会。那一次我的失手,将我推入了重重深渊......

一脸胡涂
连载中· 42.14万字
苏宇穿越到妖兽肆虐的高武世界,没有太大野心,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 但造化弄人,一家人在郊游时,遭到兽潮侵袭。 女儿重伤昏迷,自己修为尽废。 本已绝望的他,却意外激活了【安度晚年系统】。 “我才三十啊,暗度晚年系统什么鬼?” 【宿主女儿已去世七十年,请找到女儿的墓地,在她墓前倾诉思念……】 【叮!为女儿扫墓任务已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SSS级特殊体质——大道烘炉·无相骨!】 【宿主与妻子已经离婚70年,请见妻子最后一面……】 【叮!与前妻道别任务已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SSS天赋——悟性逆天!】 【……】 再面对重伤昏迷的女儿、伤心欲绝的妻子时。 苏宇对未来重新信心! 老婆先别急,我马上就无敌!

均秋
连载中· 60.49万字
【无系统】+【有仇必报】+【热血玄幻】+【后悔流】 叶洞被道侣陷害,而他敬若女神的绝美师尊,不仅没有为他洗白冤屈,反而冷眼旁观。 只因道侣攀附上了一方势力,他沦为了弃子。 这一日,叶洞被废修为,逐出宗门。 但岂料他因祸得福,反而获得了帝品丹田。 叶洞发誓,此大辱必百倍偿还,不然道心不稳!

北极大鹅
连载中· 44.76万字
萧安意外穿越到了唐朝,美丽人生正式启程? 不,是厄运的开始! 开局被陷害成为废婿,将死之际被长公主救下。 凭借自身努力,一步步逆天改命。 挽大厦之将倾扶狂澜于既到。 重整大唐辉煌。 最终,抱得美人归走向人生巅峰!

西伯利亚火鸡
连载中· 20.73万字
我叫萧器,男,之所以强调性别,是因为我患上了男性只有1%概率才会碰到的乳腺癌。 本以为生命就此走到尽头。 没想到手机里突然出现一款电子女友养成游戏。 于是就此开启我的放纵氪金之旅,存款花光,那就借网贷来充,反正已经命不久矣,钱财留着无用。 直到某天,蓝星开始和游戏世界开始融合,我才发现自己培养的电子女友,竟是来自修仙世界的女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