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让他当鬼差的!
七麒
连载中· 162.26万字
卷王驾到,都给我卷起来,人间在卷,地府也得卷,卷王到来,诸邪退避,我是地府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本书又叫《我在地府混编制》》《地府搅屎棍!》《逆袭,从小鬼到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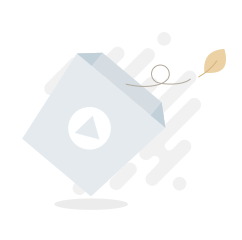

七麒
连载中· 162.26万字
卷王驾到,都给我卷起来,人间在卷,地府也得卷,卷王到来,诸邪退避,我是地府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本书又叫《我在地府混编制》》《地府搅屎棍!》《逆袭,从小鬼到阎王》

牛刹
连载中· 28.69万字
第一人格:普通刚毕业社畜;第二人格“”杀伐果断凶戾暴力!第一人格:没有卖不了的房;第二人格:没有干不死的鬼! 第一人格:大哥,有啥要求我一定满足;第二人格:碍我事者,人,干之;鬼,斩之! 一个普通卖新房的置业顾问,机缘巧合的成了专门销售凶宅的二手房经纪人。凶宅有鬼?不怕,关门,放第二人格!

深依
连载中· 27.20万字
五年前,江家在一场商业争斗中一败涂地。 江知颜从天之娇女瞬间坠入地狱,公司被夺、负债破产,父母相继惨死… 而她唯一信任的未婚夫也成了帮凶,在后背插刀,毫不留情的给了她致命一击。 那场车祸,她本不想活,却为腹中意外的生命而振作。 她逃离是非,拼尽一切,才得以重新开始。 五年后,生活步入正轨,她带着孩子回来了。 随之归来的,还有仇恨—— 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们,谁也别想好过。 她受过的痛苦,她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哪怕不择手段…

黄粱
连载中· 387.93万字
被开除警队的落魄侦探侯伟、初入警界的新人刑警石晴雪,在命运的安排下,迥然不同的俩人相遇、相识、相知,在消除隔阂中,他们渐渐逼近残酷的真相......

御风楼主人
连载中· 26.43万字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出现的短暂和平时期。但因为多年战乱,死伤惨重,人世间凶灵横行,加之时局不稳,国民政府腐败,老百姓水深火热,魑魅魍魉遍地。玄门术界最大的相术家族麻衣陈家,派出二十岁的陈汉生以相士身份行走江湖,凭借家传相术秘籍《义山公录》和六相全功,解决各种诡异事件。这位被后世尊为“神断先生”的麻衣传人,开启了一场独属于他自己的传奇经历……

笑斯人
连载中· 268.18万字
穿越十八年,本以为这是普通古代世界,计划发展成为地方豪强,作威作福。 不曾想,诡异树妖降临,万物采集程序启动,修仙的神秘世界全面打开! 今天开始,我不当地主了!叫我仙人大人,把你们的宝物、灵石、女人通通交出来!

狼吞虎噬
连载中· 98.46万字
洪天赐在出生当日,他遭遇了妖物灰仙的算计,寿命被夺, 他爷爷是风水高手,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历尽千辛寻回一口狐棺,爷爷说:里面住着他的妻子……

睡不醒的猫猫
连载中· 11.66万字
魔道天骄江厌,穿越异世悟透生存铁则——放下道德,法力无边! 地牢之内,他血阵锁魂,将正道金丹仙子炼为傀儡;师门上下,他恣意横行,连疯批师兄都甘当靠山。 “小师弟,放手去干!天塌了有师兄兜着!” 当星宿剑派神剑压宗,生死比斗迫在眉睫; 当泛海书院天骄挑衅,无名岛矿脉暗潮汹涌—— 江厌把玩着指尖血符,笑得肆意张狂: “仙子当剑,师兄扛刀,这魔道,我修得可比谁都通透!” 【黑暗流+反套路仙侠】 没有圣母桎梏,只有杀伐随心! 看疯批师兄弟如何把“不讲武德”玩成通天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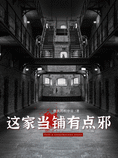
熬夜的程序员
连载中· 120.31万字
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财富、权势、爱情,机关算尽! 人的欲望无序且混乱,妒忌、色欲、慵懒,不择手段! 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 当你踏进这家老古的典当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你眼前打开,或许你能实现夙愿一方通行,或许你会坠入深渊,永恒堕落。